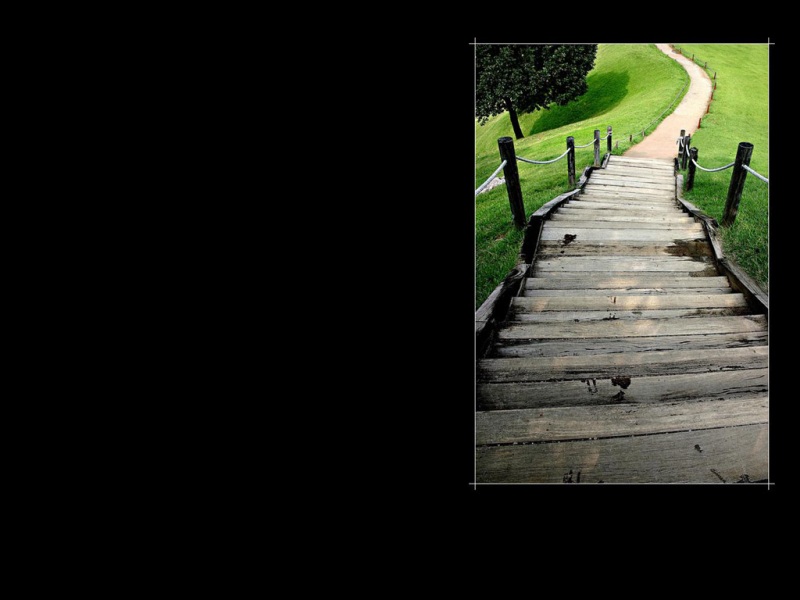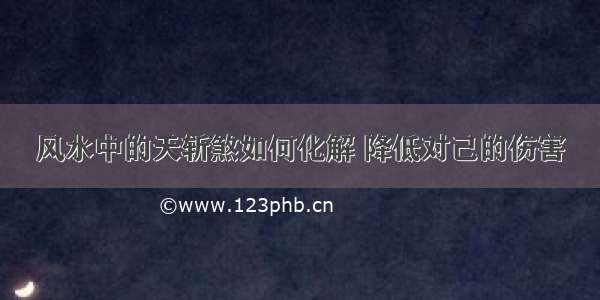“It from bit symbolizes the idea that every item of the physical world has at bottom — a very deep bottom, in most instances — an immaterial source and explanation… In short, that all things physical are information-theoretic in origin and that this is a participatory universe.”
John A. Wheeler, 1990
撰文 | 蔡荣根、阮善明、杨润秋
一、背景:It From Qubit?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和时空的基本结构、相互作用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所以物理学诞生始,物理学家们就一直在努力寻找描述从大到宇宙、小至微观粒子的基本规律。可是何为“基本”?著名物理学家约翰·惠勒(John Wheeler)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1]提出了一条三字“箴言”——“It From Bit”(万物皆比特) 。这条“箴言”建议我们从信息理论中提取新的思想,来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统一起来。
在这之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这简单而深刻的洞见在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中展示出越来越多令人惊讶的证据。比特的概念也逐渐地让位于量子比特(qubit),进而产生了进化版的三字箴言——“It From Qubit”(万物皆量子比特)。,在西蒙斯基金会(Simons Foundation)的资助下,高能理论物理学家和量子信息学家,这两个通常不会有交集的群体走在了一起, 开始了名为“It From Qubit” 的研究计划[2]。这里“It” 可以理解为时空。这个想法暗示时空可能并不是最基本的概念,而是从更为基本的量子比特中呈现(emerge)出来的。在这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AdS/CFT (anti-de Sitter/Conformal Field Theory)对偶和量子纠缠(quantum entanglement)。
AdS/CFT 对偶描述了引力理论和量子场论之间的一种对偶关系。它由 Maldacena 于1997年根据超弦理论提出的一个猜想发展而来。简单来说,这个对偶表明一个d维时空的共形场论(CFT)和一个 d+1 维的渐进反德西特(AdS)时空中的引力理论是等价的。这个对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引力理论研究中一个十分活跃和重要的研究方向。量子纠缠则是描述了量子态之间的特殊关联性。它是量子系统区别于经典系统的一个重要性质。例如两个量子比特组成的 EPR 态 (也被称作“Bell态”或者“猫态”)
是由两个纠缠在一起的量子比特构成。无论这两个纠缠的量子比特相距多远,我们一旦知道了其中一个量子比特的状态,另一个量子比特的状态自然就知道了。爱因斯坦将这种“奇异”的现象称为“幽灵般的超距作用”(“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
为了定量地描述量子态中纠缠的强弱,人们引入了“纠缠熵”的概念。纠缠熵与AdS/CFT虽然属于两个完全不同领域,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一对概念蕴含着深刻的内在联系。Shinsei Ryū 和 Tadashi Takayanagi 在提出了“全息纠缠熵猜想” [3]。在这个猜想中,d+1 维反德西特时空边界上的子区域 A 的纠缠熵,等于这个子区域延伸到时空内部的最小面的面积(如图1所示), 亦即:
这里 GN(N为下标) 是 d+1 维时空中的牛顿引力常数。这样一个公式与黑洞的贝肯斯坦-霍金熵(Bekenstein-Hawking entropy)公式非常相似。
图一:d+1 维反德西特时空的 d 维边界上CFT理论的一个子区域 A 的纠缠熵等于这个子区域延伸到在 d+1 维的时空内部时的最小面的面积。
它不仅暗示了时空几何与纠缠熵之间存在关联,而且开启了“It From Qubit”研究的大门。基于此研究,Maldacena 和 Susskind 在合作提出了新的迷人猜想
ER = EPR
其中左边的“ER”是爱因斯坦-罗森桥(Einstein-Rosen bridges)的简称,这里代指广义相对论中大名鼎鼎的“虫洞”。右边的“EPR”则是 Einstein、Podolsky 和 Rosen 三人名称的缩写,这里代表量子力学中的量子纠缠。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个数学或者物理方程式。它更像一个标语——强调量子纠缠和时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如果这种联系存在的话,那么它不仅可以自然地把现代物理学的两大基石——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联系起来,而且也暗示了量子纠缠在时空结构的呈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图二:虫洞的艺术图片。连接左右两个时空的区域就是虫洞,亦即爱因斯坦-罗森桥(ER)。| 图片来自 Tomáš Müller for Quanta Magazine
“It From Qubit” 项目的宏大目标是期望可以通过量子信息的概念来理解时空的呈现,从而最终通过量子的观念来描述引力。理论物理学家对这个目标的追求已近百年。爱因斯坦在发现相对论之后就投入到对这个最终理论的追求,可是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也未成功。现在看来,“It From Qubit”尽管离最终的殿堂也还遥远,但是它最大的意义或许在于开启了许多崭新的、值得追寻的方向。
二、量子信息:计算复杂度?
在 Shinsei Ryū 和 Tadashi Takayanagi 指出 AdS/CFT 对偶中时空与纠缠熵的关系之后,全息纠缠熵的研究在过去十几年中一直是高能物理中的热门研究方向之一。年已古稀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Susskind 在产生了不同的想法。Susskind认为,我们应该在全息时空中或者“It From Qubit”的框架下考虑不同于纠缠熵的概念。他认为一个被称为“复杂度”的概念就是这样一个候选者。
“复杂度”这个概念最早来源于计算数学领域,被用来刻画完成算法的难易程度,进而对计算问题进行分类。常用的度量复杂度的量有计算所需要的时间、算法需要的基本运算的数目等。量子电路中,复杂度则由电路中所含有的基本量子逻辑门(quantum gate)的数量来度量。
虽然复杂度的概念起源于计算科学,可是不同于关心算法的计算科学家,高能物理学家关心的则是从一个初始量子态 |ΨR(R为下标)> 到目标量子态 |ΨT(T为下标)> 的复杂度。例如我们选取 N 个量子比特的简单态
作为初始的量子态。这样的态可以理解成N枚全都是正面向上的硬币组成的态。目标态则是其它可能的复杂态,如
在将上述初始态转变为目标态的过程中,最简单的基本操作就是反转一个比特的态。显然在这样的设定下,所需最少的基本操作的数目就是目标态中“1”的个数。在量子理论中,纯态之间的转换由幺正的算符U 表示。所以实现从初始态到目标态的转换就是在构建一些特定的幺正变换以满足
“复杂度”这个概念在量子信息中有着重要的应用。利用它我们可以研究量子计算的速度。在量子系统中,信息以“量子比特”的形式储存在一系列量子态中。因为量子计算的速度依赖于单位时间内能对量子态实施基本操作的数目,所以复杂度随时间的变化率正好可以用来刻画量子计算的速度。量子信息理论中对于复杂度的研究表明,一个平均能量为 E 的系统每一秒钟最多可能实施 4E/h 次改变系统量子态的操作[4]。这里h是普朗克常数,约等于 6.63×10^-34J·s。这个上界一般被称作 Lloyd 上限。它给出了在给定能量的系统中量子计算的速度所能达到的上限。
在上面的介绍中,我们考虑的是离散的、有限自由度系统。但是理论物理学家感兴趣的量子场论(QFT)却是一个无穷维的连续系统。如何将复杂度应用到QFT中呢?这时我们需要借助黎曼几何[5, 6]——它是研究广义相对论时的重要数学工具。在黎曼几何中,两点之间距离最短的连线被称为测地线(geodesic)。例如,平面中的测地线就是直线。在黎曼几何的框架下,我们可以将初始态和目标态看作态空间中固定的两个端点;两者之间不同的幺正变换则可以由其间的不同曲线表示;曲线的长度则代表了需要的量子门的数量。这样寻找最优量子电路的问题就转化为寻找最短路径的问题,亦即求解黎曼几何中测地线的问题。
三、复杂度与黑洞物理
我们已经看到“复杂度”这个概念起源于计算科学和量子信息领域。那么它为什么会被引入到黑洞物理和 AdS/CFT 对偶的研究当中呢?故事还要从上文提到的 Susskind 和 Maldacena 提出的“ER=EPR”猜想以及 AdS/CFT 对偶开始说起。
在一个含有虫洞的渐进AdS时空中,连接了左右两个时空的爱因斯坦-罗森桥(ER)显著地依赖于黑洞内部的几何,它的体积会在很长的时间内近乎线性地增长。AdS/CFT对偶告诉我们:一个渐进反德西特时空和其边界上的量子场论等价。因此,从AdS/CFT对偶的角度来看,爱因斯坦-罗森桥的演化应该对应于边界上某种物理量的演化。一个看似有道理的想法是,爱因斯坦-罗森桥的演化对应着纠缠熵的演化。不过 Susskind 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Susskind认为,仅仅用量子纠缠来描述是不够的(entanglement is not enough! )[7, 8]。因为纠缠熵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增长,并很快达到极值,所以纠缠熵无法体现爱因斯坦-罗森桥体积的变化。Susskind认为计算科学中的“复杂度”似乎正好能够用来描述爱因斯坦-罗森桥能够在很长时间近乎线性演化的现象。他与合作者先后提出两个不同版本的猜想,将时空中的几何量和场论的复杂度联系起来。这两个猜想可以简单地由几个字母表示:
C=V 或者 C=A
它们分别被称为“复杂度-体积”(Complexity-Volume)猜想[9]和“复杂度-作用量”(Complexity-Action)猜想[10]。
为了具体介绍这两个猜想,我们首先需要引入广义相对论中广泛使用的彭罗斯图(Penrose Diagram)。彭罗斯图的基本想法是通过共形(保角)变化将无穷远处的点放在有限的区域内。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完整地表示无穷大的时空。在压缩 d-1 维的空间后,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有限的二维图表示整个 d+1 维的时空。如图三所示,在渐进反德西特时空的彭罗斯图中存在两个边界(r=∞处),并且存在两个对称的、平行的宇宙。在经典图像中,这两个宇宙只是被平凡地“堆砌”到了一起,双方并不会发生任何关联。然而 Maldacena 在其一篇论文中指出:对于一个稳态的黑洞来说,左右两个时空是纠缠在一起的[11]!纠缠就像是时空的粘合剂,将时空碎片粘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时空。从AdS/CFT对偶的角度来看,没有纠缠的时候,左右两个时空对偶的量子态就是左右两个边界上量子态的平凡直积。但是实际上由于左右两个宇宙是纠缠在一起的,因此他们对偶的量子态则是一个特殊的纠缠态,一般简称为“TFD态”(thermofield double state)
现在一个自然的问题是:我们制备这样的TFD态所需要的复杂度是多少呢?Susskind 猜测,这个复杂度可以由连接左右两边的爱因斯坦-罗森桥(亦即图三中绿色的虫洞)的最大体积来表示,
图三:渐进AdS-黑洞时空的彭罗斯图。图中四个区域分别是黑洞、白洞以及两个平行的宇宙;蓝色的线代表黑洞的边界,即视界;绿色的线代表虫洞,连接了左右两个宇宙。
这里L是一个具有长度量纲的量。这就是 CV 猜想。在这个猜想中,由于复杂度直接与爱因斯坦-罗森桥的体积相关,所以它包含了黑洞内部的信息——这正是纠缠熵难以描述的部分。CV 猜想中的复杂度和前文中提到的全息纠缠熵相似,他们都是由纯粹的几何量来描述,并且不涉及物质相互作用的细节。这使得复杂度的计算变得相对简单。可是这样一个猜想并不如全息纠缠熵那般“完美”,因为这其中仍然包含了任意性:长度量纲 L 无法由理论唯一确定。这促使了Susskind 和合作者们更多的思考,并进一步提出 CA 猜想。在这一版本的猜想中,全息复杂度不再由虫洞的体积描述,取而代之的是引力理论的作用量
图四:渐进AdS-黑洞时空的彭罗斯图。图中由红色类光超曲面包围的区域即是 Wheeler-DeWitt 区。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作用量并不是整个时空的作用量,而是在一个特殊时空区域中的作用量(如图四的红色区边界内部的区域)。这个区域一般称为 Wheeler-DeWitt 区 (WDW patch)。特别是,基于“复杂度-作用量”猜想,Susskind 和布朗等人通过考虑全息复杂度的时间演化发现,黑洞恰恰可以看作是最快的“量子计算机”——因为渐进反德西特时空中史瓦西黑洞的复杂度变化的最终速度刚好能够达到前文所说的 Lloyd 上限。
和 CV 猜想相比,CA 中复杂度不再是简单地由时空的几何给出,而是直接包含了物质相互作用的细节。另外它不仅涉及到黑洞的内部信息,还涉及到奇点附近的性质和时空整体的因果结构。从表面上看,CA 猜想不像 CV 猜想那样存在任意选择的长度尺度。这个特点曾是 CA 猜想比 CV 猜想更受青睐的一个原因。可是最近更为细致地研究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由于 WDW-patch 含有类光边界,我们恰恰又需要引入一个任意的长度尺度 L 以保持作用量在类光面上的“重参数化不变性”[12]。因此在CA猜想中依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任意性。目前对于这两个猜想本身的性质以及它们是否真的可以描述 TFD 态复杂度的问题还仍然处在热烈探讨之中。
四、结束语
虽然“复杂度”这个概念正在吸引越来越多来自引力理论和量子场论领域的研究人员的兴趣,但是将复杂度的概念应用到黑洞和量子场论中来也面临着许多障碍。不同于在量子系统甚至是无穷维量子场论中定义良好的纠缠熵,复杂度在量子场论框架下的定义仍然存在许多不清楚的地方。这也导致通过全息对偶计算得到的复杂度的物理含义并不十分明确。在利用AdS/CFT对偶计算复杂度时,CV猜想和CA猜想得到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目前尚无法判断哪一个猜想更为正确。相关的研究也表明,CA猜想得到的复杂度的增加率可以违背量子信息理论中复杂度增加率的上限。
不过这些不足不仅没有使人们在研究黑洞的时候放弃“复杂度”这个概念,反而激发了人们对其进一步研究和改进。在最近的研究中,“复杂度”被运用到更加广泛的领域。比如布朗等人发现复杂度在一般系统中也会满足一个类似“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定律[13]。迈尔斯等人则提出了一个复杂度版本的“第一定律”[14]。通过将复杂度和张量网络相结合,人们发现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杂度与时空以及引力的动力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5]。在通过几何化方法研究共形场论中的复杂度时,研究人员发现共形场论中的复杂度等价于二维引力的Polyakov作用量[16]。现在复杂度成为了黑洞物理、引力理论和量子场论研究等领域一个活跃的研究课题。
复杂度作为高能物理中的新概念,或许现在对其在理解量子引力和时空起源中所扮演的角色作出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是它为从量子计算和量子信息的角度去理解时空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视角,它或许能够成为理解时空起源和黑洞量子性质的一把新钥匙。
后 记
文小刚
It from bit 的原始意思是万物起源于比特。这篇文章把 It 解释为时空,讨论了时空是不是也能起源于比特?事实上,我们发现时空不能起源于比特。但最近十几年的理论物理研究强烈地暗示着,时空可能起源于量子比特,而时空连续的幻象可能起源于量子比特之间的纠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量子比特,因为经典比特没有量子纠缠。很多时空的几何概念,如面积、测地线等等,都有其量子纠缠的对应。
我们的时空是有其特定的动力学性质的。它的扭曲所形成的波应当满足爱因斯坦的波动方程。但我们对于时空动力学性质的理解还有欠缺,目前还找不任何一个(有良好定义的)量子模型能给出满足爱因斯坦波动方程的引力波。这就是理论物理中有名的量子引力问题——即使有名的超弦理论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有的超弦理论没有良好的非微扰定义,另外一些理论虽然能给出引力波,但还要加上其他许多波。它们给不出我们所熟悉的时空,其扭曲只包括引力波和电磁波。
和电磁波类似,引力波也只有两个横波模式,而没有纵波模式。不同的是,电磁波的两个横波模式是两个矢量型的偏振模式,而引力波的两个横波模式是两个张量型的偏振模式。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量子模型,它能给出有两个张量偏振的引力波和两个矢量偏振的电磁波,而不附带其它我们时空中没有的波。这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量子引力问题。
近二十年,凝聚态物理的研究在这方面给出了一些进展。首先,通过对高温超导体的研究,我们找到了量子比特模型(弦网模型),它能给出有两个矢量偏振的电磁波,而不附带其它的波。后来许岑珂有了一个突破性的发现, 他构造了一个量子比特模型,能给出有两个张量偏振和一个纵模的波。我和顾正澄又找到一个改进的量子比特模型,能给出只有两个张量偏振的波。这已经和引力波很接近了,但我们模型中得到的这个波,不像引力波那样具有一个固定不变的速度,我们的波速度跟其频率的平方成正比。这导致它不满足爱因斯坦的引力方程,而是满足 Lifshitz 引力方程。所以量子引力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左)许岑珂(右)顾正澄
回到 It from bit 的原意:万物起源于比特。那构成万物的基本粒子,如电子、夸克、光子等等,到底能不能起源于比特?答案是不能够。但万物,以及这些基本粒子,可以起源于量子比特。比如通过上面提到的量子弦网模型,我们发现纠缠的量子比特可以产生只有两个矢量偏振的电磁波(其对应于光子)。电子、夸克这些对应于物质的基本粒子也能起源于量子比特。其实上面讲的弦网的密度波对应于光波,而弦的端点正好对应于电子、夸克这些物质粒子。除了引力子,我们发现万物(即组成万物的基本粒子)的确可以起源于量子比特。(详见《返朴》文章“拓扑序:看世界的一种新视角”)。
作者介绍:
蔡荣根: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黑洞物理,引力理论和宇宙学。发表文章260余篇,共计引用15000余次。
阮善明:加拿大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在读,师从著名学者Robert Myers教授。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硕士毕业,目前研究兴趣为场论中的复杂度定义和复杂度与时空几何的关系。发表多篇重要工作。
杨润秋:韩国高等研究院博士后,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博士毕业。目前研究兴趣和方向是场论复杂度定义和全息复杂度,在相关领域发表多篇有影响力的文章。
参考文献
[1] J. A. Wheeler, Information, physics, quantum: the search for links, in Complexity, entropy, and the physics of information (W. Zurek, ed.), pp. 309–336, Westview Press, 1990;
[2] “It From Qubit”, Simons Collaboration on Quantum Fields, Gravity and Information. Project Introduction (/mathematics-physical-sciences/it-from-qubit/projects/) and Research Proposal (http://web.stanford.edu/~phayden/simons/simons-proposal.pdf);
[3] S. Ryu and T. Takayanagi, Holographic derivation of entanglement entropy from the anti–de Sitter space/conformal field theory correspondence, Phys. Rev. Lett. 96 (), no. 18 181602;
[4] S. Lloyd, Ultimate physical limits to computation, Nature (London) 406(2000) 1047;
[5] M. A. Nielsen, M. R. Dowling, M. Gu and A. C. Doherty, Quantum computation as geometry, Science 311 () 1133-1135;
[6]Jefferson, Robert A., and Robert C. Myers. 'Circuit complexity in quantum field theory.' Journal of High Energy Physics .10 (): 107.
[7] Susskind, Leonard. 'Entanglement is not enough.' Fortschritte der Physik 64.1 (): 49-71.
[8] 纠缠熵本身只是纠缠这样一个量子概念的一种度量方式,更严格地说这里只是强调了 “entanglement entropy is not enough”;
[9] L. Susskind,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and Black Hole Horizons, Fortsch.Phys. 64 () 44–48;
[10] A. R. Brown, D. A. Roberts, L. Susskind, B. Swingle and Y. Zhao,Holographic Complexity Equals Bulk Action?, Phys. Rev. Lett. 116 ()191301;
[11] Juan Martin Maldacena, “Eternal black holes in anti-de Sitter,” JHEP 04, 021 ()
[12] Lehner, Luis, Robert C. Myers, Eric Poisson, and Rafael D. Sorkin. 'Gravitational action with null boundaries.' Physical Review D 94, no. 8 (): 084046.
[13] A. R. Brown and L. Susskind,“Second law of quantum complexity,”Phys. Rev. D 97,no. 8, 086015 ();
[14]A. Bernamonti, F. Galli, J. Hernandez, R. C. Myers, S.-M. Ruan, and J. Simon, “First law of holographic complexity,” Phys. Rev. Lett. 123 (Aug, ) 081601.
[15] B. Czech, “Einstein Equations from Varying Complexity,” Phys. Rev. Lett. 120, no. 3, 031601 ();
[16] Caputa, Paweł, and Javier M. Magan. 'Quantum computation as gravity.'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22, no. 23 (): 231302.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